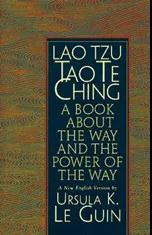道教经籍在西方世界的译介经历了三个高潮: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基督教话语体系的独白、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西混合话语体系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道教话语体系的建构。 前两次译介高潮的推动力分别是早期西方传教士传教的需要和20世纪前期拯救西方社会的需要。如辛红娟在《〈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一书中提出,“在卫礼贤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的崩溃,而拯救战后西方文明的‘良药’只能是来自中国的道家文化,老子的微言大义已经开始被引入欧洲文化的肌理”1。因此,这两次译介高潮的根本推动力均源自外部,对中国而言,都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译介的根本目的也在于通过译介、引用东方文化来构建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2,在这两个时期很少有学者或译者从道教经籍自身来研究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发展。在这些译者眼中,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中国是一个“他者”。“反映在翻译领域,就是西方的译者通常采用贴近目的语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翻译策略”3,如采用基督教的术语和概念来理解道教的核心观念。“在一种文化外传的初期,这种‘误读’是正常的,而且一定的误读会促进文化传播。”4但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这种以牺牲道教话语体系为代价的译介策略越来越难以满足宗教文化传播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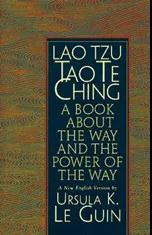
《道德经》英译本(厄休拉·勒吉恩译)

《认识道教》西班牙语版

1921年卫礼贤的译书单
第三次译介高潮的产生原因则与前两次有着本质的差别,其推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更加注重与其他国家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因此,这一时期道教经籍的译介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地”做出选择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译介中,无论是对于原文本的选择,还是指导译者的主流译介思想,亦或是译入语话语体系的建构,都与以往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前两次道教经籍译介高潮的指导思想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那么第三次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产生道教经籍第三次译介高潮的另一重要推动力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的出土和湖北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考古发现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于《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高潮,不少学者基于新出土的版本重新翻译了《道德经》,并据此对老子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力推动了道教经籍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在西方各国,较早进入第三次道教经籍译介高潮的是德国。1972年中德建交后,德国的汉学研究掀起了一个新高潮,汉学研究的发展带动了道教经籍的德译活动。以《道德经》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每年至少会有一本全译本出版,研究老子思想的书籍更是不胜枚举。其影响也由哲学、宗教扩展到文学、物理、政治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的道教经籍翻译同样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至2004年,美国《道德经》的译本数量就已超过50本,还有近20本英译本分布在其他地方的英语文化圈。其他道教经籍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被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 在前两次翻译高潮中,译介主体以西方译者为主,目的是通过译介中国典籍来印证西方文化的普适性,同时期华人译者的译介思想也是通过证明在东方文化中并不缺乏西方文化体系的思想、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来证明东方文化的存在价值,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中国文化身份重构。这种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相似性来证明中国文化价值的方法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作为基准文化的西方文化具有超出中国文化的价值。 因此,前两次道教经籍译介高潮都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框架内产生的。这种文化间的比对在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直接体现就是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早期译者试图将道教经籍的价值和话语体系比附于西方宗教文化的价值与话语体系,此时期的译本大量采用了西方话语,特别是用基督教的话语体系来比附道教,这种比附必然会牺牲道教经籍所承载的话语体系,从而导致道教经籍自身宗教文化价值的丢失。 而中国道教的价值恰恰在于两种宗教的差异性,正是这一差异性构成了道教经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意义,即将道教经籍独特的宗教价值传递到译入语国家,在译入语中重构道教经籍的话语体系。在道教经籍前两次译介高潮中,许多译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道教自身文化特征的传递和道教经籍话语体系的重构,译作不仅未能传递道教经籍的独特价值,反而为西方宗教价值、话语体系的普适性提供了证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经籍进入第三个翻译高潮,译介主体的国籍背景、职业背景、性别等日趋多元化。华人译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西方译者和华人译者合译的情况逐渐增多。同时,在日渐国际化的中国,能够进行道教经籍译介的中国本土译者不断增多,进行道教经籍外译现象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加。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功底的华人译者和中国本土译者从中国宗教的内在脉络来理解道教经籍,因此能在翻译中照顾到原著的本义,发现此前译者所忽略或不很了解的独特之处,将原作固有的哲学和宗教精神表现出来。而西方译者则可以保证译文的语言质量和在译入语读者中的可接受性,因此,这一时期的译文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这一时期,翻译的目的不再是为西方服务,而是在世界宗教舞台上展示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宗教,进而弘扬和传播中国的道教文化。译者开始重视原文本来承载的价值和话语体系,有意识地利用道教的思想、术语来建构中国本土宗教的话语体系,进而在异域文化中建立起独特的本土典范,使道教在世界上成为独立存在的、有自身价值的宗教,而非依附在西方话语下的西化道教,从而向西方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在世界话语资本的争夺和再分配中,为中国宗教的话语资本争取一席之地。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道教经籍的外译本中,中国本土宗教的话语体系雏形初现。许多译者在翻译道教经籍的核心概念时,为了避免读者误读,直接采用音译的形式,如托尔伯特·麦克卡罗(TolbertMcCarroll )在1982出版的英译本中将“无为”音译为“Wu-Wei”。建构中国道教话语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主流翻译的目的。 这一时期道教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实现途径有三个:一是对原文版本的考证和对原文本的研究;二是道教经籍核心概念的异化翻译策略;三是原作思想价值体系在译本中的建构。 这一时期的翻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译者为了准确把握原作的思想和内涵,更加重视原文本的选择和对原文本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中西方译者在翻译中都不再以一个底本为准,而是以一个底本为蓝本,同时参考原作的其他版本,以及与原作相关的研究,有的译者还在翻译中参考其他译者的译本或其他语种的译本,这一做法反映了译者更为严谨的译介态度,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尊重。如美国畅销书作家、翻译家史蒂芬·米切尔于1988年翻译《带前言和注释的〈道德经〉》译本时就参考了前人的英译本、德译本和法译本。 在道教经籍核心术语处理方面,许多译者开始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于汉典籍的外译,徐珺教授指出,“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抵抗式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待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译者应时刻牢记自己作为译者所肩负的职责和义务,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用异化策略来处理原文。如果出现归化-异化两可的情况,应优先异化策略”5,并据此提出了在中国典籍翻译中“要大胆使用中国英语,从而填补由于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表达真空”6。 道教经籍中有许多术语在西方语言中没有对应语,早期的译本往往借用西方词语表达,这一策略在道教经籍外传初期较为适用,因为过多使用迥异于西方话语的语式,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障碍。但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和传播的深入,在读者有了一定的接受基础以后,就应逐渐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读者译介真正的异域文化。 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应进行相应的术语创新。术语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零翻译的策略。这一策略体现了文化互相交融的特征与趋势,是构建道教话语体系的有效途径之一。在道教经籍的第三次译介高潮中,许多译者采用了零翻译的策略,而在零翻译中,音译是最为常用的一种。 以道教经籍基本概念“道”字的翻译为例,该字含义极为丰富,迄今尚无学者穷尽其终极意义,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意义和用法都对等的词语非常困难。对此,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提出,“道”这一概念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关于形而上的概念无法找到完全对等物7。在前两次译介高潮中,“道”在不同的目的语中,译法多样。以英语为例,“道”被译为“Way”“Road”等。20世纪80年代后,译者逐渐认识到,无论用任何一个词汇来对译,都会损失掉其他含义,无法传达汉语中“道”的多重丰富内涵。因此许多译者和汉学家都采用了音译的方式,以涵盖其丰富而模糊的意思。这一方法既可保留“道”的丰富含义,又能实现道教经籍概念的一致性,是实现道教经籍本土宗教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20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中西方译者放弃了韦氏拼音法,直接将其译为“Dao”,如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在《道教思想的西方嬗变》一书正文中,全部采用“Dao”和“Daoism”来表示“道”和“道家思想”。对道教经籍中出现的人名也全部采用现代汉语拼音,如“Zhuangzi”。康思奇更是明确指出,应该纠正道教经籍在西方传播中的误译现象,改变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话语体系,对道教经籍中的文化负载词用现代汉语拼音进行“音译”,从而解决道教经籍翻译中对中国宗教的误读问题,同时实现道教经籍翻译中的术语统一。8 除音译外,移译也是零翻译范畴的概念,在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过程中,此类翻译方法的使用,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中的文化色彩,传播道教思想与文化,从而体现出原语的文化价值。 采用零翻译策略还可以解决道教经籍译介过程中对同一概念译法不统一的问题。道教经籍涉及的概念极多,其中许多概念的具体含义随文本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出现了对同一概念译法不统一的情况。对于无法阅读中文原著的西方读者,很难把一词的多个译法联想到同一个概念上,更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该词在原文中所承载的整个概念体系。零翻译策略的采用统一了对同一概念的译法,确保了概念和命题的一致性,从而推动了在译文中原文话语体系的重构。 但在道教经籍的初传期,对于缺乏原语文化背景的普通读者而言,零翻译策略容易带来困惑,当困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零翻译对于读者而言就真的近于零了,翻译也就此失去了意义。 因此,在这种翻译策略指导下翻译出来的译文,只适合具备一定原语文化背景知识的读者群,其目的是在译语文本中建构中国道教的话语体系,提高中国话语还原能力,让读者接触到真实而非西化的道教文本。 道教话语体系在译本中的建构不单反映在语言的处理方式上,更深层面的是体现在译者对原作所承载的价值体系的认知和对原作思想的理解上。在这一点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和美国汉学家安乐哲。 葛瑞汉在译介庄子的过程中,首先考察了《庄子》自身所承载的价值,发现了《庄子》中蕴含的理性论辩。葛瑞汉认为,“由庄子的著作可以看出,庄子更类似于古希腊的智者,从不执着于任何固定的立场,热衷于指出论辩中的陷阱”9。在翻译庄子的《齐物论》时,葛瑞汉一直以这种相对主义的模式来考察原作的思想,其英译本《齐物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中的一系列论辩,清晰晓畅地传递出原文中隐含的论点,将一个具有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庄子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正是从葛瑞汉开始,西方译者和汉学家开始真正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古代思想。 针对用西方的宗教思想体系来解读中国典籍的现象,安乐哲也明确指出:“有意或无意地将文本从其自身历史和文化土壤中移栽到另一个决然不同的哲学园地是对该文本的严重冒犯,对其生命之根的损害是深重的。”10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很多共性,但在宗教和哲学层面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在翻译中未能发现和承认这种差异”11,将会“致使我们(西方人)对中国的世界观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12。 葛瑞汉和安乐哲虽然没有直接从宗教的角度对《庄子》承载的道教话语体系进行分析,但从其对原作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译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典籍自身所承载的价值,从而为在道教经籍外译本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 笔者对20世纪以来的《道德经》英译本进行了抽样分析,选取样本的标准是:第一,译文不能是转译本;第二,译本必须是《道德经》的全译本;第三,译本影响力大、具体评判标准为再版次数多、发行量大、出版后评价较多。根据上述标准,共选定50本英译本,并据其首版时间分为1900至1979年之间的译本(16个)和1980至今的译本(34个)。通过对比原文中“道”“圣人”“象帝”等3个词语在这两个时期的英译情况,分析了20世纪英译本的话语体系变化状况。 在1900-1979年间的16个译本中,有11个将“圣人”一词译为“thesage”或者“the holy man”,占采集样本的68.8%。这两个英语词汇均具有神格意谓,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神学气息。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4个译本中,有18个译本将其译为“thesage”,占采集样本的52.9%,其他译本均采用意译的方式,用形容词“wise+名词修饰语”的方式,从而将“圣人”一词的汉语意思“睿智,明智”表达了出来。若对21世纪以来的《道德经》英译本单独进行统计,则可发现,带有神格意谓的英译比例更低,仅占41.7%,中国话语更为凸显。在翻译该词时,采用中国话语方式的译本已上升至54.6%(其中有一译本将该词略译)。 在这一时期的英译本中,道教的话语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核心概念的翻译中,借用西方概念的情况逐渐减少,中国道教的话语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国与世界的宗教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道教经籍的外译在重塑中国宗教形象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其外译本是世界了解中国本土宗教的重要窗口,大多数读者因语言障碍无法理解原文,译本是他们了解道教的重要途径,对道教概念的理解也都源自译本中的对应词,因此译介思想和译介策略直接决定了译本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道教经籍的译介过程中,随着原语文化所在国家与译入语文化所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对比的变化,不同时期、不同国籍的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即便是同一原著,译本所产生的话语体系也截然不同。事实上,道教经籍外译本的话语体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嬗变所体现的是中外文化软实力的博弈过程。因此,在新的译介高潮中,译者应该努力建构中国本土的宗教话语体系,在世界宗教舞台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 (作者单位为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19年03期。)1. 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1页。2. 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4-5页。3. 黎土旺:《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7期,第53页。4.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宗教哲学交流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 219页。5、6. 徐珺:《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汉文化经典外译策略探讨》,《外语教学》,2009年第2期,第 88-95页。7、10、11、12. 安乐哲、郝大维著,何金俐译:《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64页。8.Komjathy,Louis:Daoist Texts Translation,P1,http://www.daoistcenter.ors/Articles_files/Articles_pdf/Texts.pdf.9. Graham,Angus Charles Graham:"be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Compared withshi/fei and yu/wu in Chinese Philosophy, Asia Major, NS7, Nos.1-2(1959),(Graham, 1959:79-112).